【编者按】“下馆子”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活动,餐馆也是人类文化中非常古老的一部分。“餐馆史”从来不单是美食的故事,餐馆本身就是映照社会历史变迁的“镜子”。两位美国饮食文化研究的权威历史学家,以全球史与跨文化研究的双重视野著书《下馆子》,向我们展现了餐馆中的菜单制定、厨师烹饪、侍者服务、设备更新、经营模式等各方面的历史变迁,多角度呈现了熟悉却不曾了解的“下馆子”那点事儿。
经出版社授权,本文摘录书中关于“世界上最早餐馆”的篇章,一同领略中国餐饮在世界餐饮史上的开天辟地之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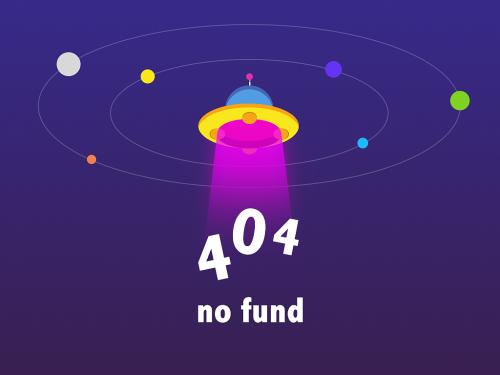
《下馆子:一部餐馆全球史》,[美] 凯蒂·罗森 & 埃利奥特·肖尔 著,张超斌 译出品方:好·奇,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年4月
古代人们外出就餐的场合——从小酒馆到套餐餐馆,从聚会场所、驿站到咖啡馆,都算不上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餐馆。餐馆的完整意义以及人们对它们的体验,依赖于服务和食物的选择。这些特征以及餐馆作为一个社会机构的功能——从最初的小酒馆、小吃店、小客栈发展到现在——已历经一千多年的时间。只有在一个可以容纳商务旅行者的足够大的重商主义经济的十字路口,城市的发展才能保证餐馆文化的完全形成。这种情形并没有在西方发生,而是发生在约1100年的中国宋朝,中国城市里第一批开设的餐馆要比巴黎餐馆的出现早700年。
为什么餐馆会起源于这里?或许最明显的答案是人口规模:北宋末期,北方的开封和南方的杭州都是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大约在同一时期,巴黎有30万人,米兰有20万人,格拉纳达有15万人,伦敦仅有10万人。
第二,中国城市居民人口所持的货币都是小面额。
第三,这些大型城市也是巨大的贸易中心,汇聚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而对于旅客和那些以城市为家的人来说,可以享用来自其他地方食物的想法成为另一个驱动力:具有21世纪餐馆文化特色的地方菜系(来自世界各地的“地道”食物),在开封和杭州这两大城市已完全形成。
第四个原因或许与政治有关:中国社会秩序的松散导致了一个由士大夫而非世袭贵族统治的中央官僚社会的出现。这群人拥有权力和金钱,却没有途径、空间或意愿留在家里娱乐。此外,由于一个人可以通过政治手腕在阶层间移动,而在餐馆吃饭就提供了理想的战略空间和见面场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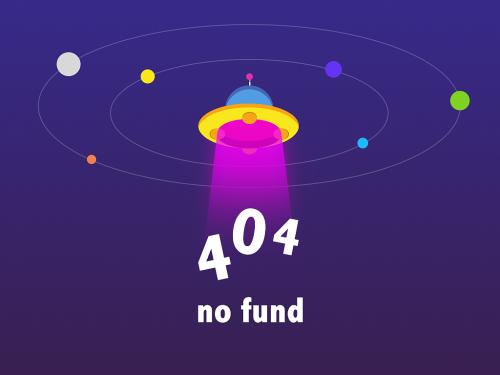
《文会图》 约1100—1125年,宋徽宗,水墨绢本。
有历史可考的最早的餐馆出现在中国开封。直到1127年,开封一直都是宋朝的首都。那些有关这座繁华城市餐馆的初期作品和绘画表明,这座城市当时已经进入了一个充斥着之前提到的小酒馆、小吃店和小摊位的时代。这些餐馆大都是与地方菜系息息相关的特色餐馆。这也在意料之中,开封的水路四通八达,除了把食物和食材带到这座城市的市场之外,它还带来了人,尤其是商人和官员。
这些旅行者和外来人口结成了正式的地方联盟,此后,地方菜馆便应运而生,宋代史料里就曾提到“南食”“北食”和“川饭”。南方的游客很难适应北方食物的口味,于是专为他们开设的小吃店也出现了。
这些城市的就餐场景千差万别。就像今天一样,一个人可以在小吃摊吃饭,也可以在一个更正式或不太正式的餐馆(或大或小)吃饭。这些不同的场所提供了五花八门的食物:汤、炖菜、肉类、素食、面食、点心或野味。它们通常位于城市人口密集区,比如开封有一条马行街,毗邻动物市场,“非常热闹,据说那里的灯光所蒸腾出来的烟雾和热气能赶跑蚊子和黑苍蝇”。1147年,北宋文学家孟元老在其回忆录《东京梦华录》中这样描述马行街和那里的餐馆:
马行北去旧封丘门外祅庙斜街州北瓦子……处处拥门,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
市井经纪之家,往往只于市店旋置饮食,不置家蔬。北食则矾楼前李四家、段家熝物、石逢巴子,南食则寺桥金家、九曲子周家,最为屈指。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寻常四梢远静去处,夜市亦有绕酸錴、猪胰、胡饼、和菜饼、獾儿、野狐肉、果木翘羹、灌肠、香糖果子之类。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子姜豉、抹脏、红丝水晶脍、煎肝脏、蛤蜊、螃蟹、胡桃、泽州饧、奇豆、鹅梨、石榴、查子、榅腉、糍糕、团子、盐豉汤之类。至三更方有提瓶卖茶者。盖都人公私荣干,夜深方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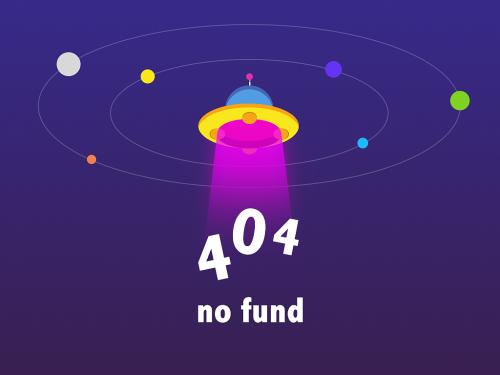
《清明上河图》局部,约1186年,张择端,单色水墨绢本。
餐馆的顾客和供应的食物通常与其所在的地点相匹配。比如在一座寺庙附近,衣饰店和书店之间一定会有一家素食茶室风格的餐馆。在妓院众多的地方,一定会有许多南方菜馆。据美国汉学家奚如谷推测,“尽管关于地方餐馆与妓院之间的实际关系信息甚少,但在城市的娱乐区,二者毗邻的现象似乎是可以预见的。”餐馆通常位于娱乐区,许多餐饮场所会专门安排从歌姬到舞台表演等多种娱乐活动。
这类餐馆大多规模较大。据奚如谷记载,某家饼店配备超过50个灶,每个灶前都有四五个工人在负责和面、捏饼和入炉。1147年,孟元老曾这样描述这种大餐馆:
大凡食店,大者谓之“分茶”,则有头羹、石髓羹、白肉、胡饼、软羊、大小骨角、犒腰子、石肚羹、入炉羊罨、生软羊面、桐皮面、姜泼刀、回刀、冷淘、棋子、寄炉面饭之类。吃全茶,饶齑头羹。
…………
又有瓠羹店,门前以枋木及花样礬结缚如山棚,上挂成边猪羊,相间三二十边。近里门面窗户,皆朱绿装饰,谓之“欢门”。
每店各有厅院东西廊,称呼坐次。客坐,则一人执箸纸,遍问坐客。都人侈纵,百端呼索,或热或冷,或温或整,或绝冷、精浇、膘浇之类,人人索唤不同。行菜得之,近局次立,从头唱念,报与局内。当局者谓之“铛头”,又曰“着案”讫。须臾,行菜者左手杈三碗,右臂自手至肩驮叠约二十碗,散下尽合各人呼索,不容差错。一有差错,坐客白之主人,必加叱骂,或罚工价,甚者逐之。
除了丰盛的食物,这段描述中最让人惊奇的莫过于训练有素的店小二。店小二们唱念顾客的菜单,以及驮叠着几十个碗的形象虽然出现在一千多年前,但如今看来依然很现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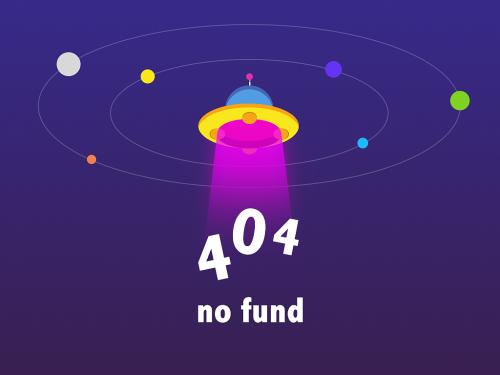
《清明上河图》局部
其他关于早期餐馆的故事则来自杭州。1132年,宋都从开封迁至杭州(当时称为临安)。马可·波罗到达那里的时候,蒙古人已经在1275年完成了对杭州的入侵。马可·波罗称这座城市为“昆赛”(quinsai),这是汉语“首都”的波斯语变体。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在其《蒙元入侵前夕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中提到这位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他把杭州描述为“昆赛之大,举世无匹……在那里可以找到这么多的乐趣,简直恍若步入天堂”。杭州城中心与之前的开封很相似,只是货物来自更遥远的海外:中东和东南亚。
除了被称为“茶酒厨房”的宴席承办者(包办饮食、餐具和装饰的餐馆)之外,还有一种大型餐馆。马可·波罗曾这样描述这种大型餐馆:
湖心有两个岛,每个岛上都矗立着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厦,其间有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房间和独立的包间。当有人想要举行婚宴或盛大的宴会时,就会在这其中的一座殿堂里操办。所有的物件都已准备停当,诸如碗碟、餐巾、桌布及其他任何用得着的东西。室内的装饰摆设都由这两座殿堂的公民共同出资兴建和维修,他们也正是为此目的而建造的殿堂。有时,这些殿堂里会同时举行100场不同的宴会,有的大宴宾客,有的庆祝婚礼;然而所有人都能在不同的房间和包间里找到很好的去处,而且被安排得井然有序,谁也不会妨碍到谁。
和开封一样,杭州城内也有餐馆和茶肆,“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以勾引观者,流连食客。”食物被盛在精美的瓷器和漆器上,小曲入耳,可谓逍遥自在(这里的女孩会唱曲,而不是像古希腊的女孩吹笛子)。约1300年,在宋朝编纂的文献《梦粱录》中,除了对餐馆本身的描述之外,还开始出现了关于人们不知如何正确点餐的故事:
初坐定,酒家人先下看菜,问酒多寡,然后别换好菜蔬。有一等外郡士夫,未曾谙识者,便下箸吃,被酒家人哂笑。
我们会在许多场合遇到“乡巴佬”(贸然闯入自己不熟悉的文化)这种说法,包括19世纪早期巴黎人通过使用出行指南和餐馆指南学会如何举止得体。对于经常光顾餐馆的新一代人来说,18世纪的中国餐馆指南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
尽管中国餐馆早在近1000年前就已经完全形成,但欧洲餐馆却还要再经过700年才会出现。在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里,从面条到瓷器,众多的饮食文化在欧洲和亚洲之间传播;然而拥有侍者、菜单、丰富的食物选择、不可思议的装饰及娱乐的餐馆并没有随之迁移。相反,欧洲餐馆的出现非常突然。更进一步讲,它们像中餐馆一样,均出现在一个丰富的场景之下:获取食物的多种方式、在公共场合一起吃饭,以及客栈、小酒馆、俱乐部和茶馆的出现等等;但却基本上没有菜单、侍者、隐私或外出就餐的礼节。